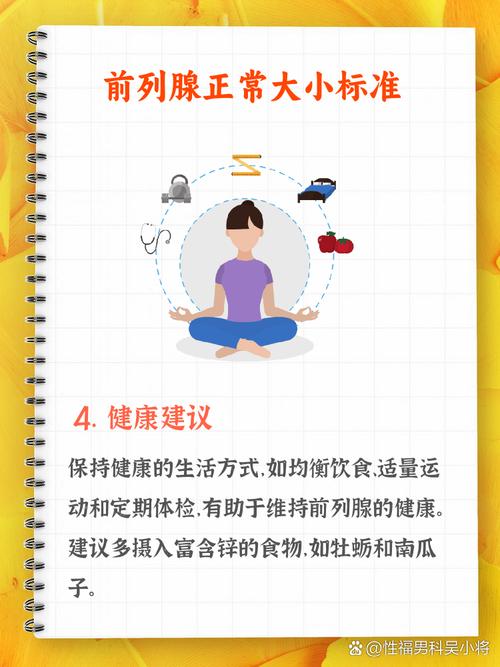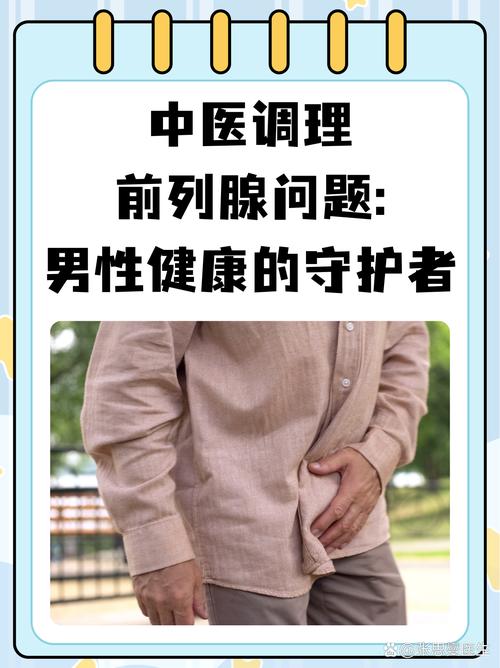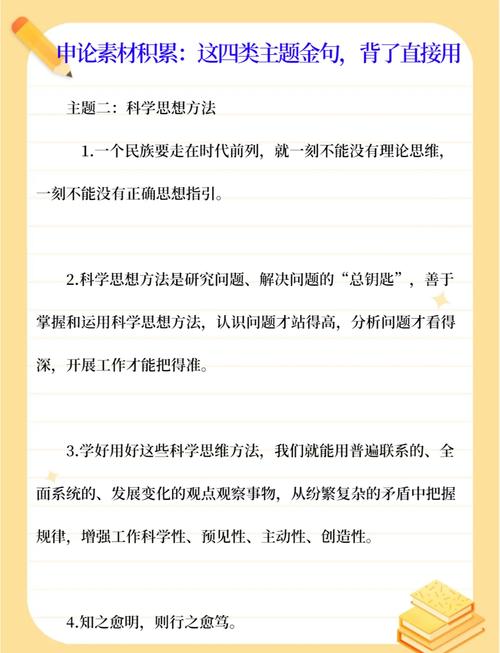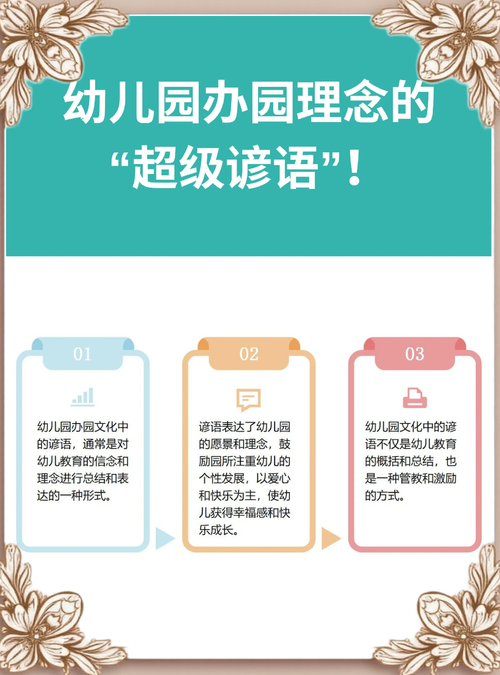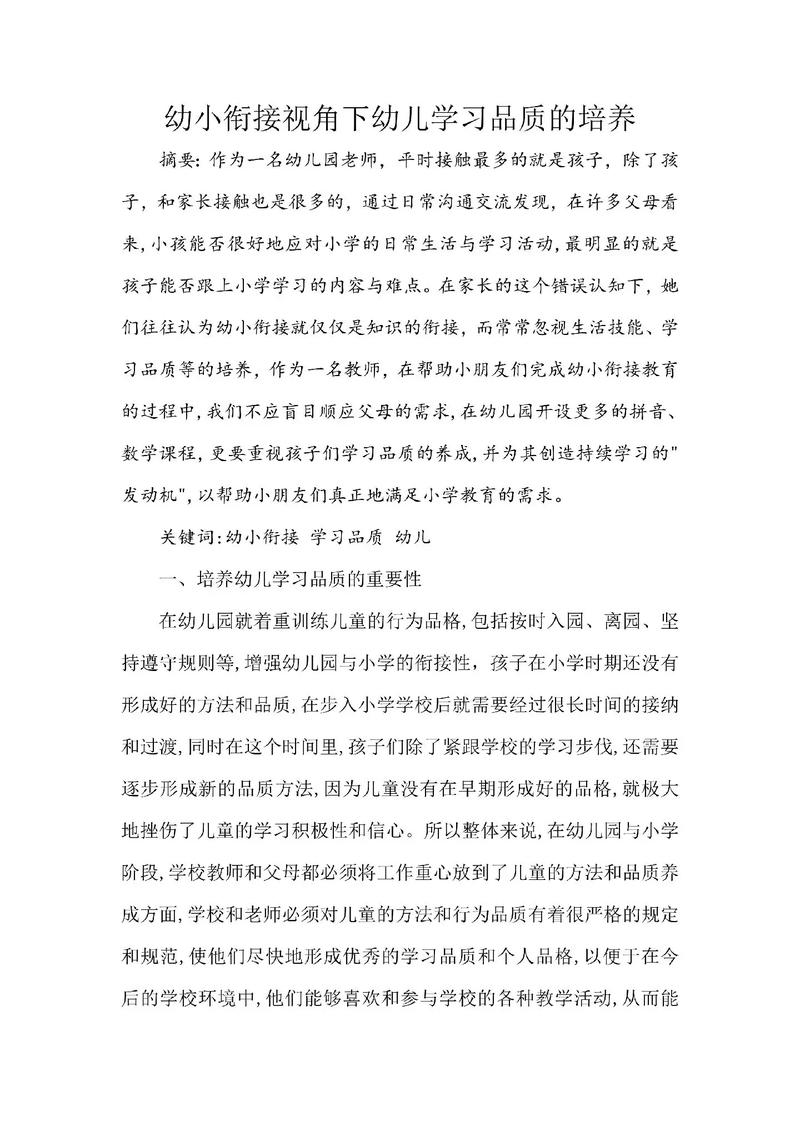科学领域的竞争如同深海潜流,表面平静却暗藏汹涌,真正站在浪潮之巅的人,往往掌握着三个核心密码:将知识结构编织成动态网络,用实验数据作燃料驱动认知引擎,在学术丛林中搭建独属于自己的观测站。
知识网络必须具备生物般的进化能力,曾有学生在研究量子计算时,偶然发现拓扑绝缘体论文中的数学工具竟能解释其生物信息学项目里的基因折叠规律,这种跨维度的知识串联不是偶然,而是刻意训练的成果——每周用思维导图将不同学科的新知进行非线性连接,就像给大脑安装知识超导材料,诺奖得主本庶佑的实验室有个传统:要求成员用三句话向其他领域研究者解释自己的课题,这种思维蒸馏法能有效打磨概念的晶核。
实验台才是真正的真理竞技场,清华大学类脑计算团队有个不成文规定:任何理论猜想必须在48小时内转化为可验证的实验方案,去年他们正是凭借这种即时反馈机制,在全球首次实现神经形态芯片的情感模拟功能,数据不是躺在论文里的标本,而是需要解剖的活体组织,当你在重复实验时发现某个数据点始终偏离预期,这可能不是误差,而是新物理规律的敲门声——就像当年暗物质存在的首个证据就藏在看似异常的天文观测数据中。
在学术丛林中建立观测站需要精准的坐标定位,MIT媒体实验室的博士生们有个独特的文献追踪法:用自研算法抓取预印本网站的最新论文,然后根据引用关系绘制知识扩散热力图,这种方法让他们在可穿戴设备领域提前半年捕捉到柔性电子皮肤的技术爆发点,参加学术会议时,别急着挤进人头攒动的报告厅,茶歇时走廊里的偶遇往往更有价值——石墨烯的突破性进展就始于某次研讨会后两位科学家在咖啡馆的餐巾纸演算。
站在实验室窗前看着天色渐明时,我常想起费曼的话:“科学是相信专家也会无知的信念。”前沿探索者真正的武器不是装满文献的硬盘,而是保持系统开放性的勇气,那些改变游戏规则的发现,往往诞生于某人决定相信自己的观测数据而非教科书结论的瞬间,保持对未知的饥饿感,让每个实验失败都成为校准认知罗盘的契机,这才是科学前沿探险者的生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