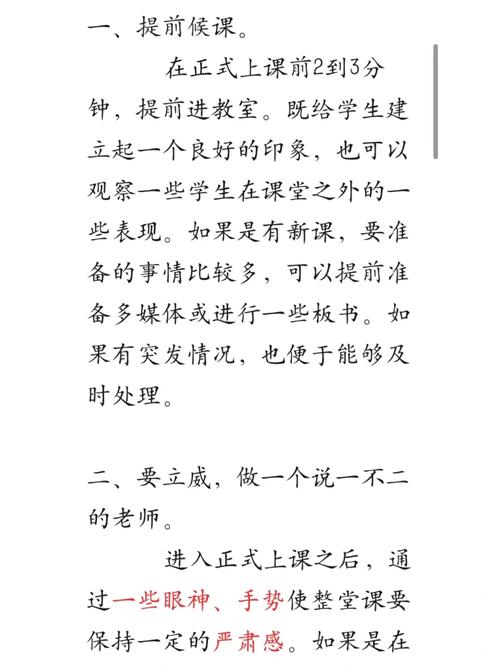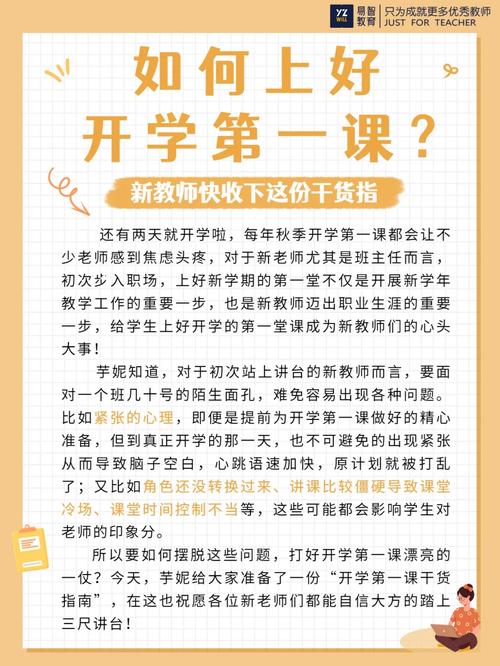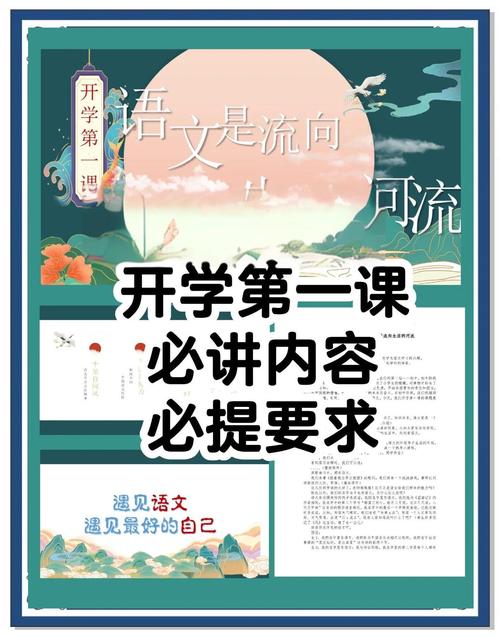经历漫长的假期后,重新回到教室的这一刻,语文课需要的不是机械的知识灌输,而是一场唤醒感知力的仪式,站在讲台上的第一分钟,我会让教室陷入短暂的寂静——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声,纸张翻动的轻响,窗外偶然掠过的鸟鸣,这些曾被忽略的细节,此刻都成为语言最原始的韵律。
复学首课的核心在于重建文本与生命的联结,当学生翻开《荷塘月色》,我不急于解析比喻手法,而是让他们闭目想象:晚风是否带着老家池塘边的水腥气?树影摇晃的节奏是否像某次失眠夜看见的月光?当某个学生颤抖着声音说“荷叶的清香让我想起外婆晒的荷叶茶”,我知道语文的根系已重新扎进生活的土壤。
知识体系的修复需要更具象的锚点,我会用半节课搭建“时空走廊”:左侧黑板贴满假期前学过的古诗文便签,右侧延伸出空白的长卷,当学生摘下《岳阳楼记》的标签,发现背面藏着疫情期间的日记片段,他们突然明白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从未远去,这种蒙太奇式的重组,让记忆不再是碎片,而是等待被点亮的星座。
课堂的最后一个环节永远是未完成的留白,分发带着墨香的方格稿纸,要求只写三行:一行抄录最能触动自己的句子,一行记录此刻教室里的某种气味或声音,一行涂抹出某种情绪的颜色,这些私密的语言标本将被封存在时光胶囊,等待期末重新开启时,见证那些悄然生长的语文灵魂。
站在重新热闹起来的教室里,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好课不是把学生拖回跑道,而是让他们发现鞋底沾着的新泥正闪烁着星光,当第一个学生指着窗外抽芽的梧桐问“这算不算通感修辞”,我知道语言的春天正在他们的瞳孔里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