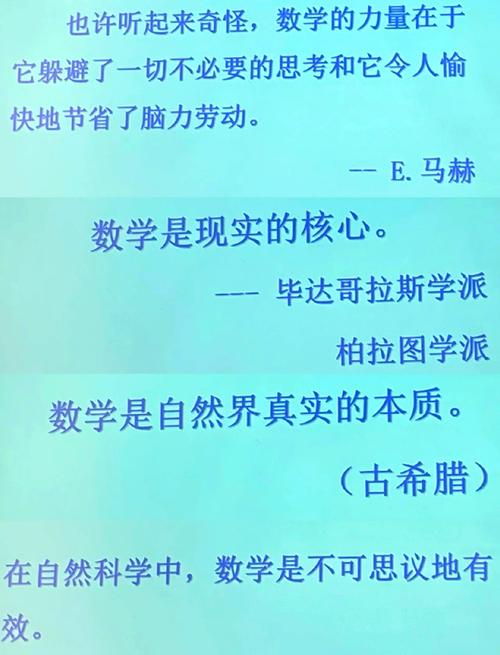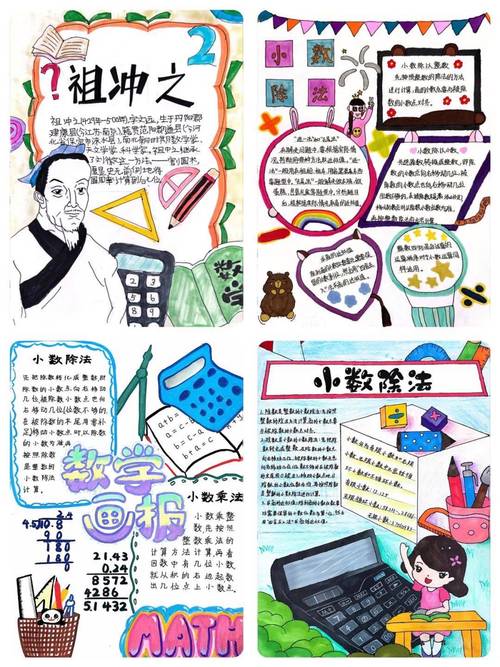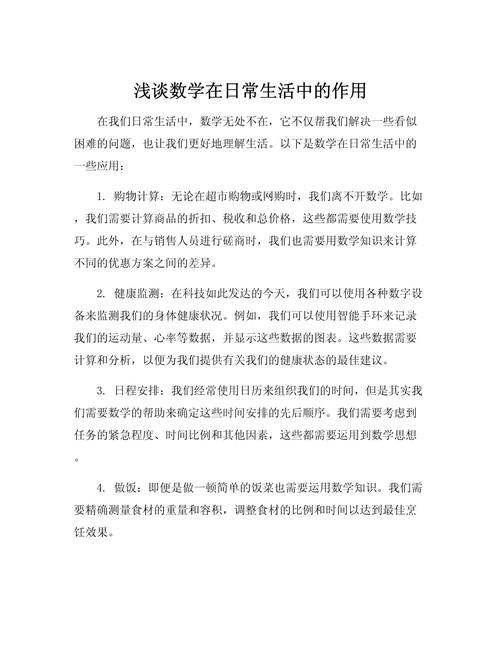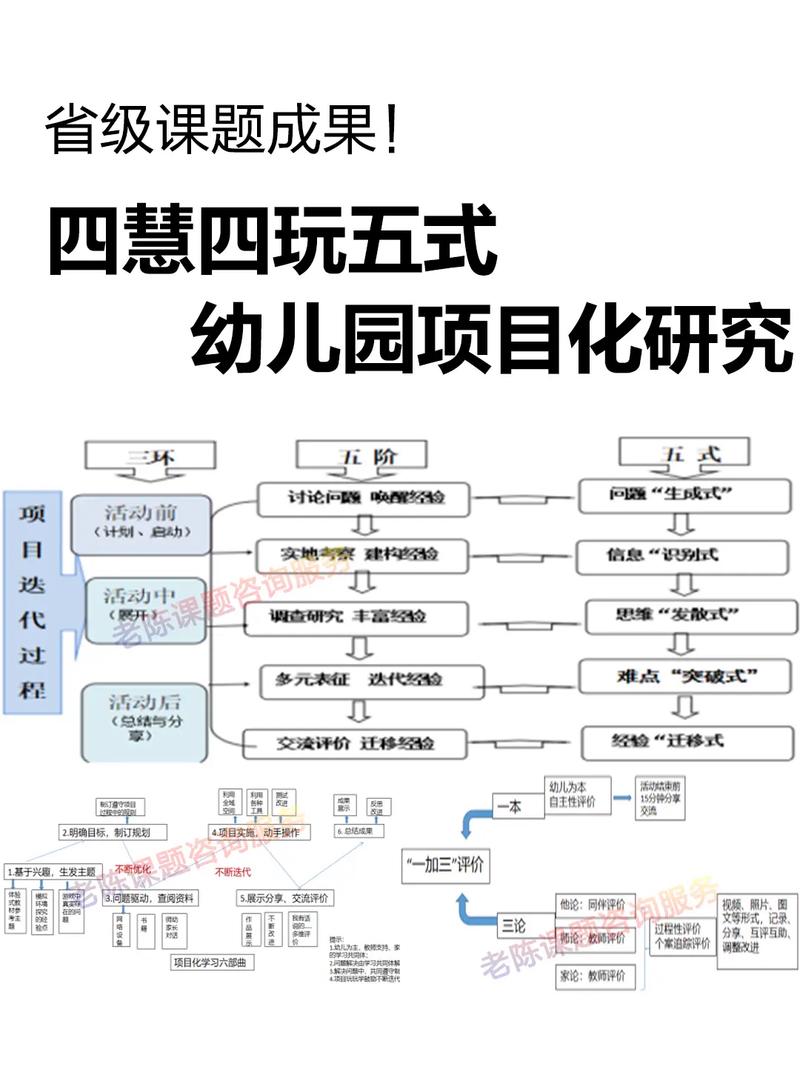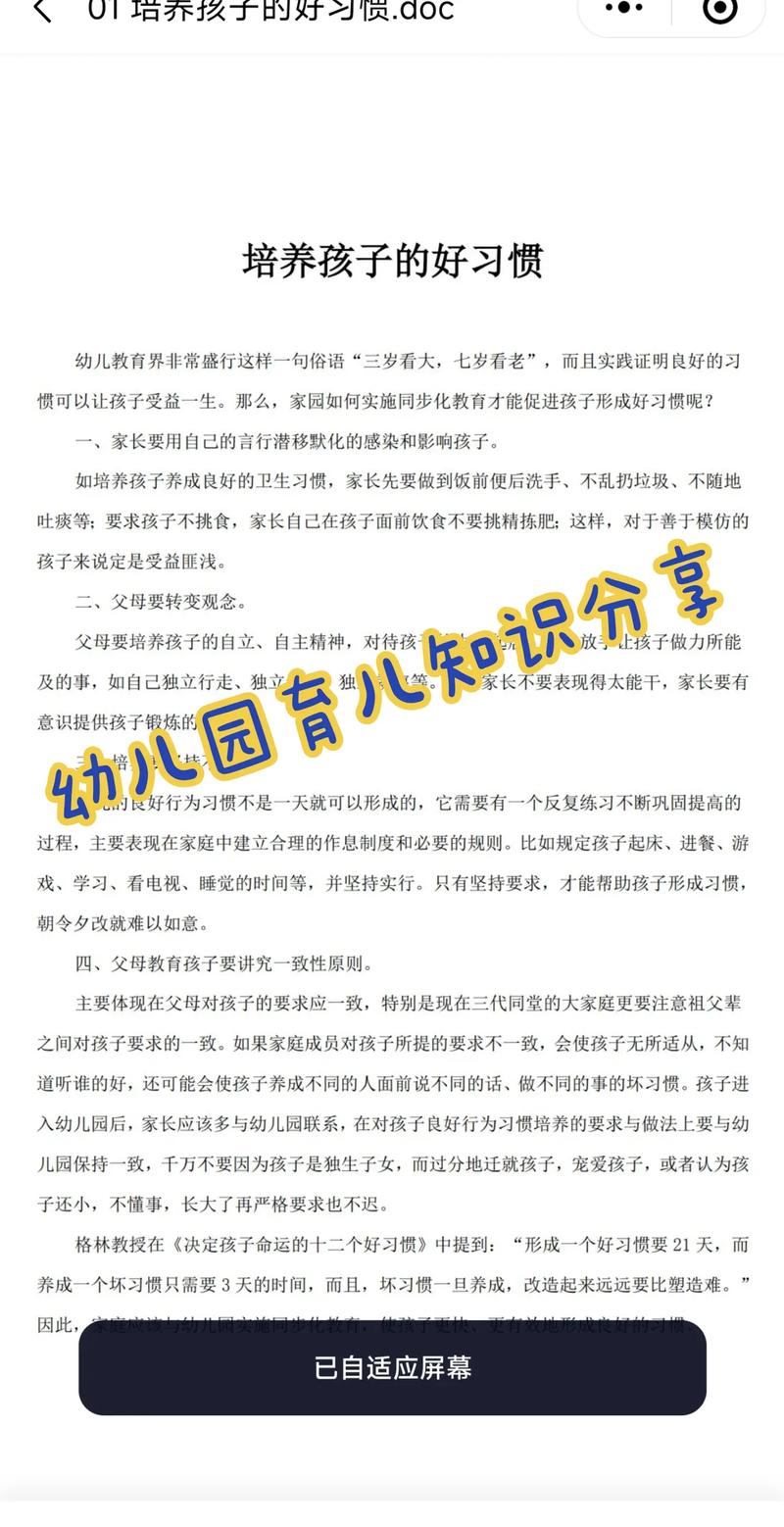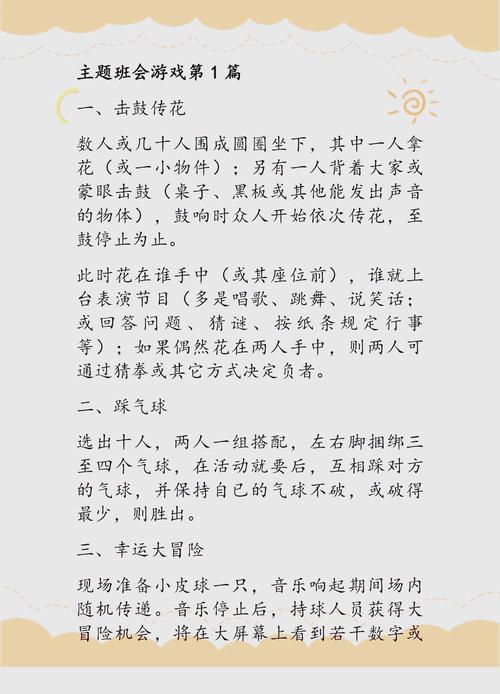在许多人眼中,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与定理的代名词,当学生翻开数学课本时,排列整齐的阿拉伯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的计算结果,似乎都在诉说着这个学科的理性与严谨,但如果我们愿意用人文视角重新审视,会发现笛卡尔坐标系里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觉醒,勾股定理的发现记录着古代文明的智慧碰撞,就连最简单的圆周率π,都凝结着人类跨越千年的执着追寻。
数学史本身就是一部文明交流史,当阿拉伯商队沿着丝绸之路将印度数字带到欧洲时,他们不仅传播了计数符号,更架起了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玛雅人用贝壳和玉米粒构建的二十进制系统,与黄河岸边用算筹推演的天元术遥相呼应,证明不同大陆的祖先都在用数学理解世界,这些穿越时空的数字对话,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地记录了人类对真理的共同向往。
翻开《九章算术》会看见"方田""粟米"等充满生活气息的章节标题,程大位在《算法统宗》里用诗歌体例编写数学题,这些细节揭示着古代数学家的人文情怀——他们始终将数学视作理解生活、改善生活的工具,就像苏步青教授在战火中坚持微分几何研究时所说:"公式里藏着民族自强的密码",这种将学术追求与人文关怀相融合的精神,至今仍在浙江大学的数学课堂中传承。
巴黎圣母院的玫瑰花窗用黄金分割创造视觉奇迹,敦煌壁画里的飞天衣袂藏着抛物线的美学密码,当达芬奇在《维特鲁威人》中描绘完美人体比例时,他其实在用几何语言诠释人文主义的核心——对人的价值与美的肯定,这些跨越学科界限的创造提醒我们,数学公式从来不是禁锢思维的牢笼,而是打开人文之门的钥匙。
站在讲台上二十年,我始终相信真正的数学教育应该让学生看见公式背后跃动的人文脉搏,当学生用拓扑学理解莫比乌斯环的哲学意味,用概率论讨论《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用词差异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数学的理性之美,更是人类用智慧理解世界时那份永恒的热忱,这正是数学最深刻的人文性——它始终记录并参与着人类文明对真善美的不懈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