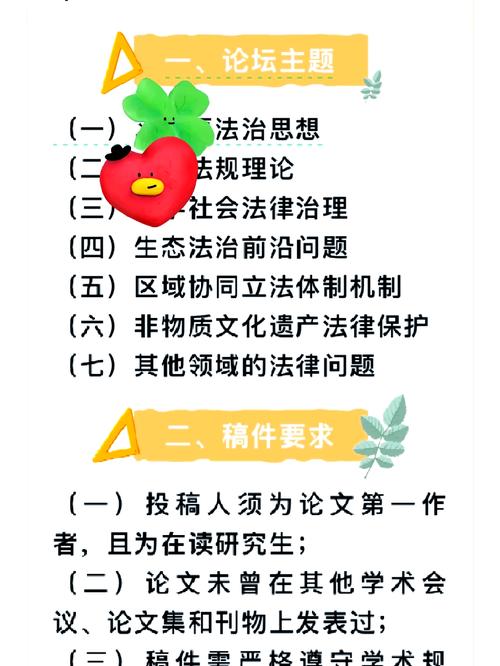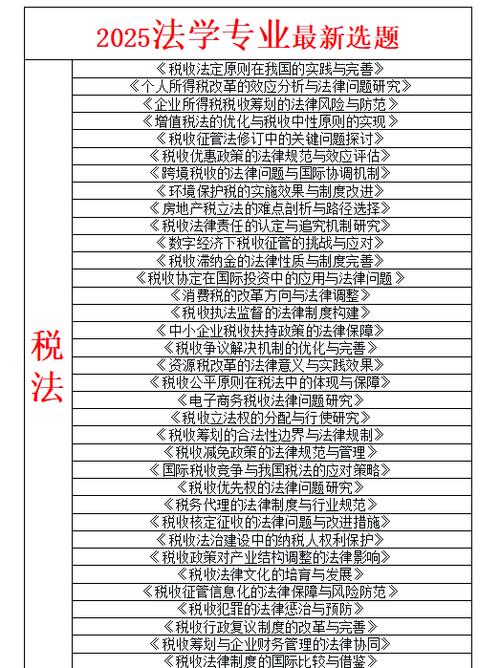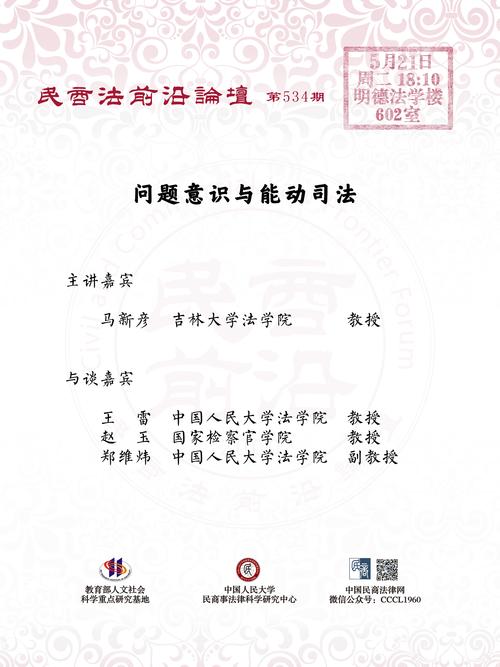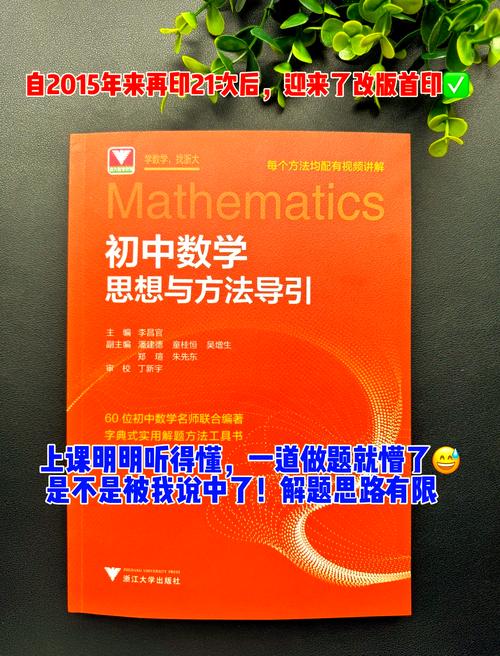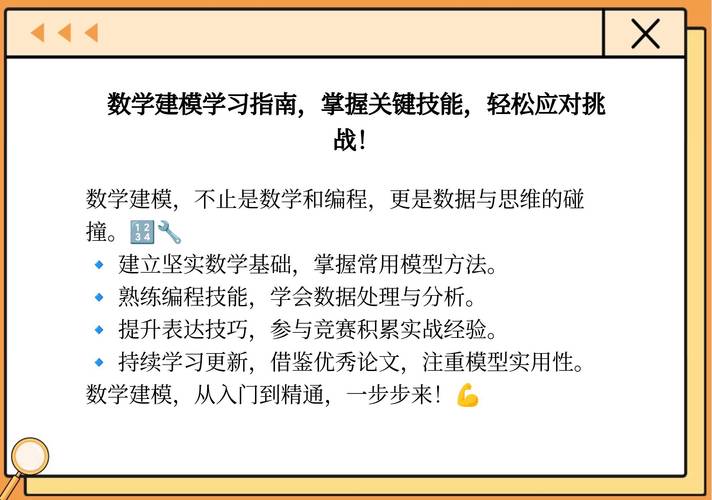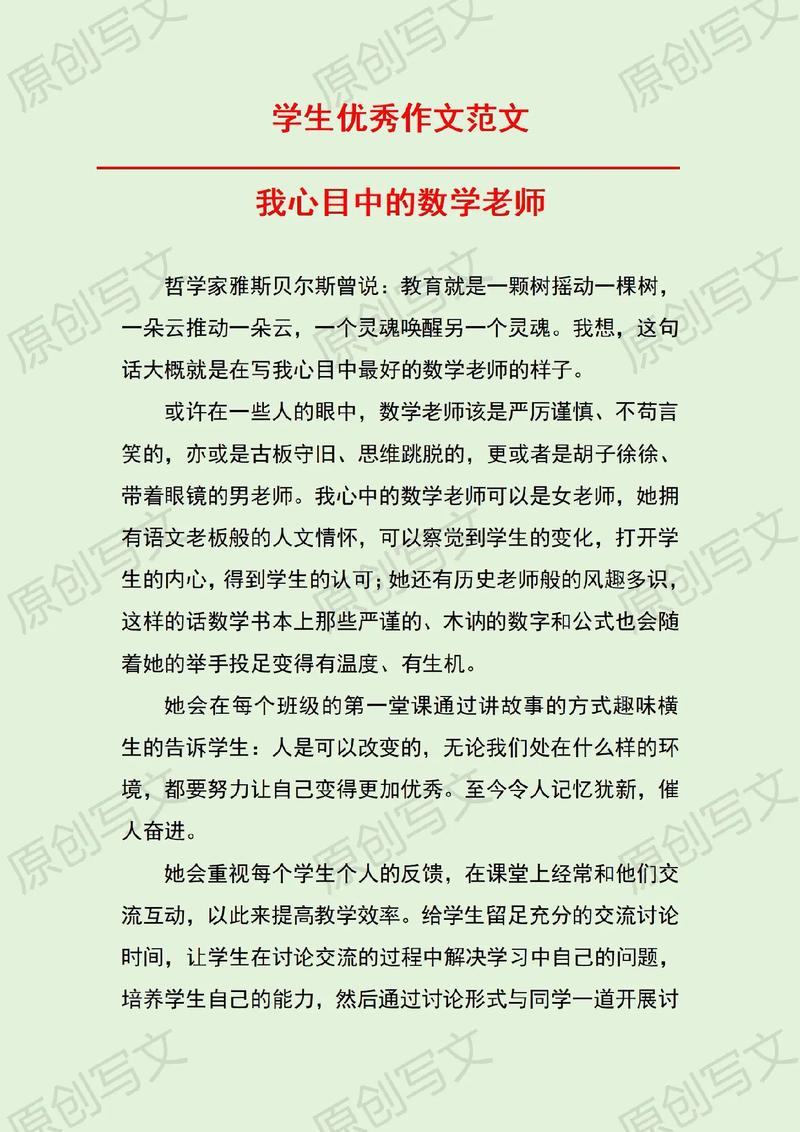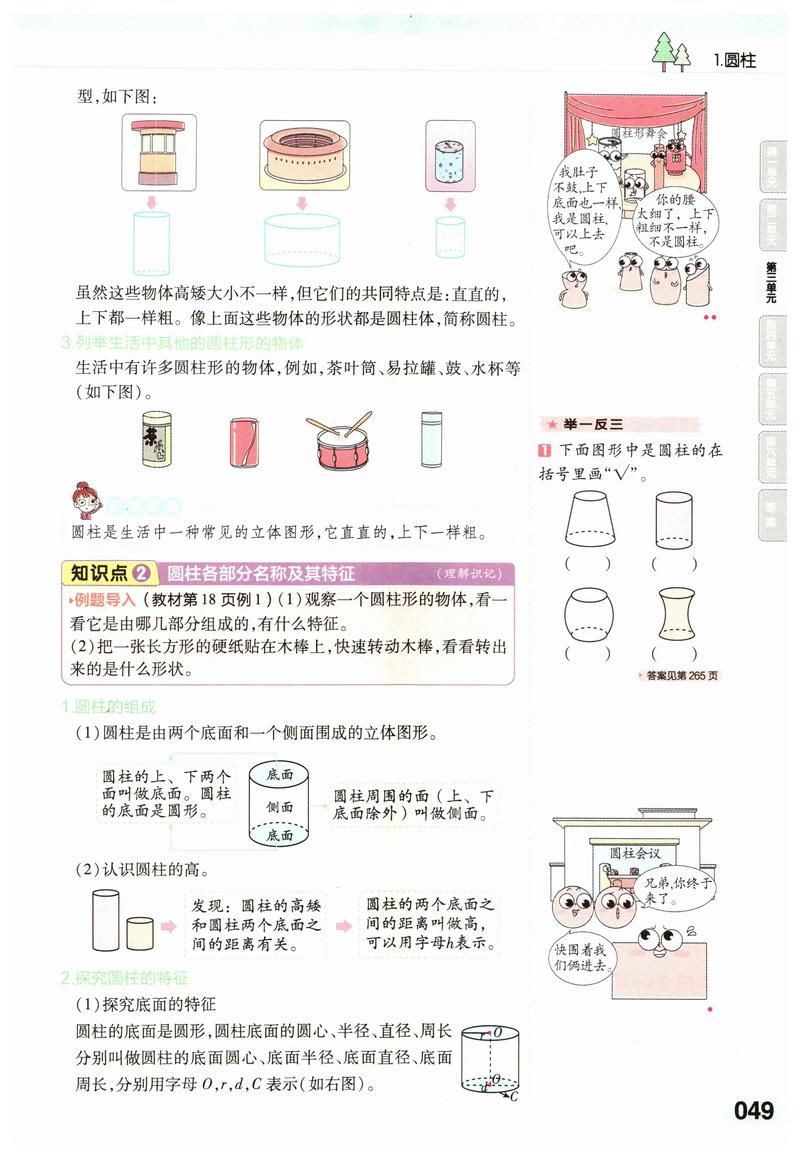站在法学院讲台第十七年,每当讲解《德国民法典》第823条侵权责任条款时,总会想起去年某自动驾驶汽车路测中误伤行人的案例,这个真实的困境恰如普罗米修斯之火,既照亮了法学演进的轨迹,也灼烧着传统理论体系的边界,当区块链智能合约开始替代公证文书,当人工智能法官系统在个别法域投入试用,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学前沿问题从来不是学术期刊里的文字游戏,而是法律人必须直面的时代叩问。
理解法学前沿问题的本质,首先要破除两个认知误区,有人将之等同于西方法学理论的简单移植,捧着德沃金、哈贝马斯的著作奉为圭臬;有人则视之为技术至上的产物,忙着给ChatGPT套上法袍,真正的法学前沿始终扎根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就像2023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立法博弈,表面是算法透明度与产业发展的冲突,实质是数字时代权力重构在法律场域的投射,这些问题的涌现,恰恰印证了霍姆斯大法官那句“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现代回响。
研究前沿问题的价值维度需要双重视角,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算法歧视案中,原告因某平台用工分配系统导致的接单量差异主张权利,这个鲜活的案例揭示着:当代码开始书写社会规则时,程序正义必须被重新定义,而在某元宇宙平台虚拟土地拍卖引发的产权争议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新型权利客体的确认难题,更是法律本体论在数字空间的自我革新,这种双重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规范法学的严谨推演,又需具备社科法学的现实洞察,就像波斯纳法官强调的,法律必须回应社会成本的真实变动。
对待前沿领域的正确姿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自动驾驶立法的审慎态度颇具启示,他们在2022年裁定中坚持:任何技术创新都不能动摇人格尊严的宪法底线,这种坚守提醒我们,研习前沿问题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对法理根基的深度开掘,就像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过程,既吸收GDPR的规制经验,又创造性设立“守门人条款”,展现了处理前沿问题的中国智慧——在传统法教义学的框架内生长出新的理论枝蔓,而非简单截取域外制度的现成枝条。
站在教室窗前,看着法科生们争论人脸识别技术的合法性边界,忽然明白:法学前沿问题本质上是时代交给法律人的考卷,它不是等待标准答案的习题集,而是需要我们用专业精神书写的法治篇章,当技术洪流冲刷着法律的堤岸,真正的学者应当如罗马法学家般严谨,如衡平法院大法官般敏锐,在变革浪潮中守护法的精神,在理论创新中延续法的生命,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法律人特有的光荣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