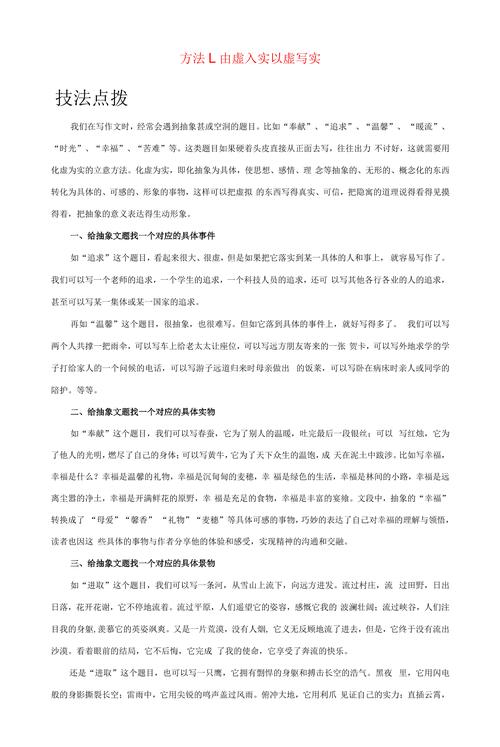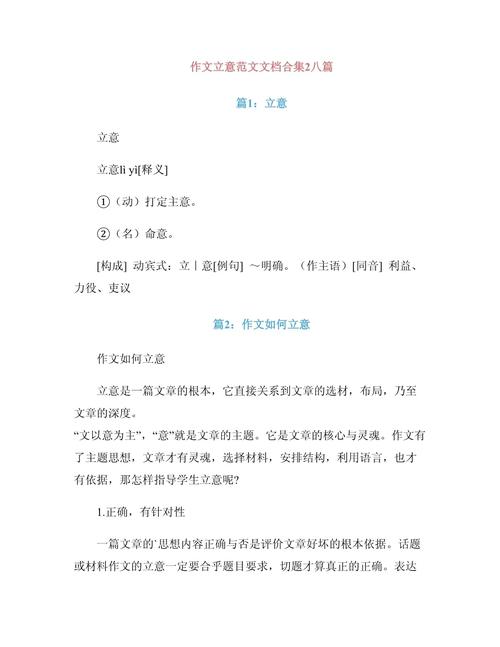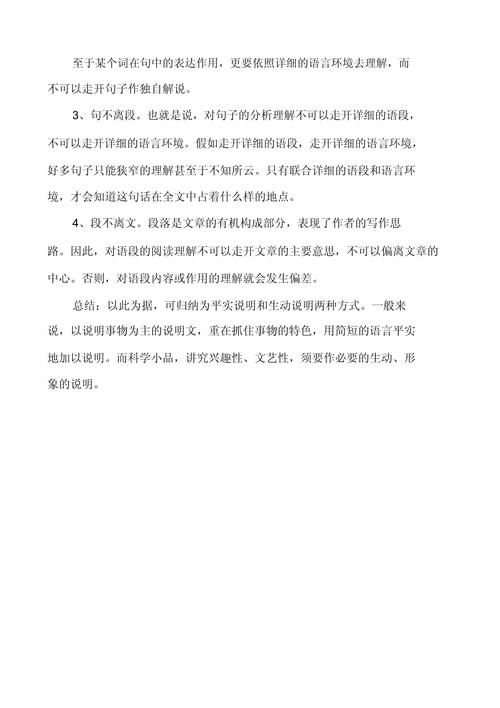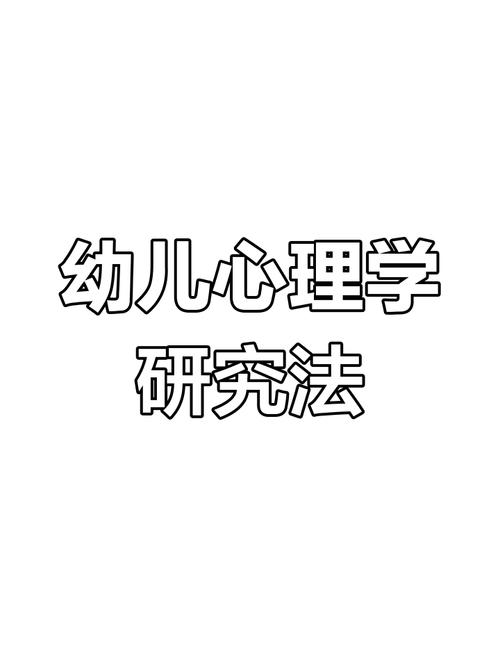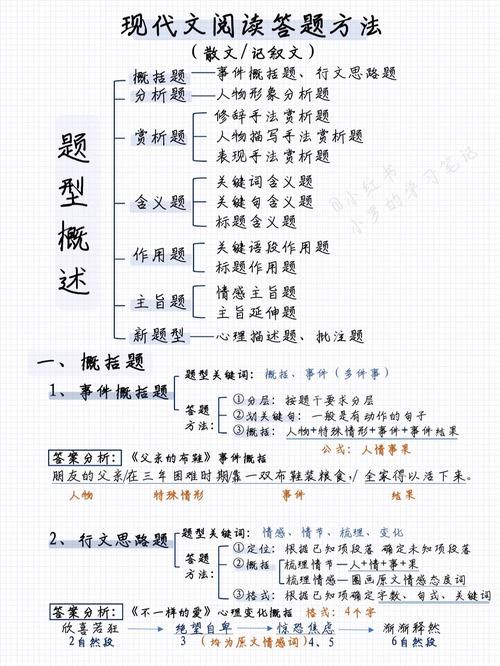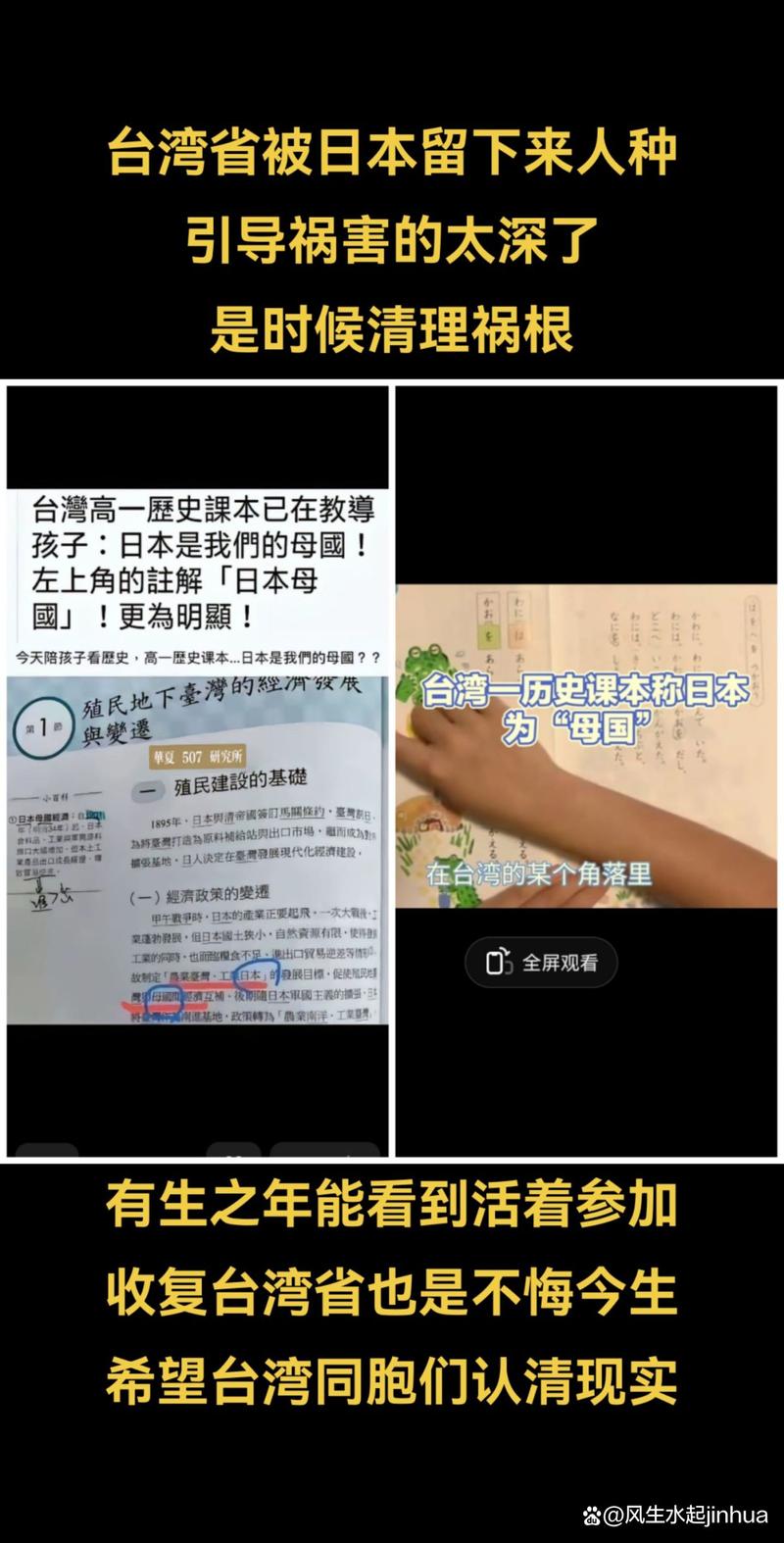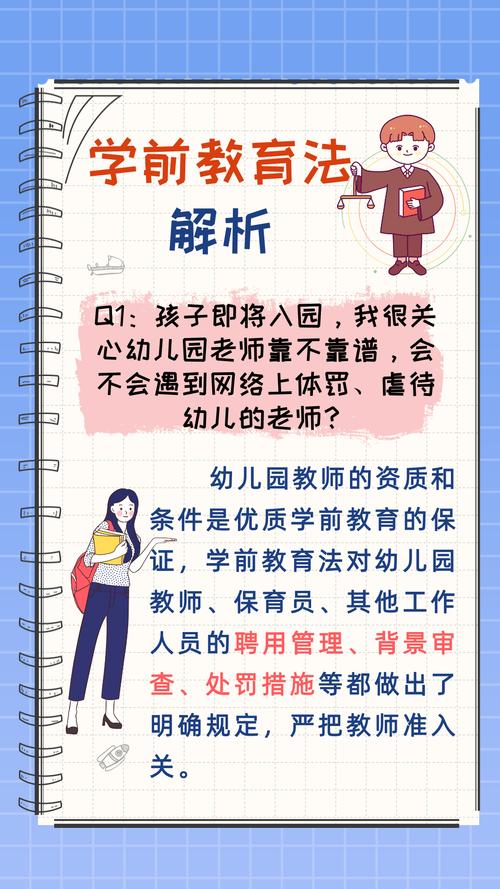作文就像一棵树,枝干是结构,绿叶是修辞,但决定它能长多高的,永远是深埋在地下的根——这个根,就是文章的立意,二十三年站在讲台上批改过三万篇作文后,我见过太多枝繁叶茂却根基虚浮的文章,也见证过最朴素的文字因立意高远而直击人心。
第一铲要挖到生活岩层
去年有个学生写"妈妈送伞",初稿里只有雨伞的颜色和妈妈的背影,我问他:"那天你鞋袜全湿却坚持上学,真的是因为'好学生必须守纪律'吗?"他愣住后突然说:"其实是怕妈妈冒雨再送第二趟。"这个细微的心理转折,让普通场景裂开一道缝隙,照见了中国式亲情特有的"双向隐藏",好立意不在远方,而在你刻意忽略的生活褶皱里。
第二铲要触到时代断层
有个女生写"故乡的老槐树被砍",初稿停留在环保主题,我建议她对比奶奶用槐花做蒸菜的记忆与推土机的轰鸣,她修改后写道:"树桩的年轮里藏着二十四节气的密码,而钢筋水泥的丛林只用温度计丈量四季。"这种时空对撞的视角,让个人记忆变成了城市化进程的微型标本,立意的高度,取决于你能否在个体经验里找到时代的切面。
第三铲要凿穿情感岩壁
批改过一篇"父亲的自行车",学生详细描写了后座的皮革纹路,却漏掉了最关键的温度——那个总提前十分钟预热车座的细节,当我指出这点,他补写道:"原来后座的热度不是阳光的馈赠,而是父爱在时间里的精准守候。"真正的好立意,是让文字拥有触感的温度,在读者皮肤上激起战栗。
第四铲要遇见未知矿脉
去年期末考作文题是"门",多数学生写防盗门象征人际隔阂,唯独有位学生写外婆总虚掩着老木门:"她说门缝里能漏进月光,还能留住游子归家的脚步声。"这种反直觉的立意,就像在花岗岩里发现了水晶簇,永远要给意外留一扇窗,最动人的立意往往诞生在预设的裂缝中。
现在我布置作文时,会让学生先交三份不同的立意提纲,有个男孩写"校园梧桐",第一稿是"季节轮回",第二稿变成"年轮里的校史",第三稿突然转向"落叶在水泥缝里扎根"——那片倔强生长的落叶,后来成了区作文大赛一等奖作品,好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不断推翻重建的思维革命。
考场作文格子框得住字数,框不住思想的野马,当你站在生活的矿脉上高举矿灯,那些闪烁的立意钻石,会自己照亮前路,这世上从没有平庸的题目,只有尚未苏醒的思考者。